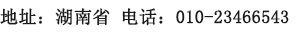1.江南大义与中国美感,为余今年花溪孔学堂驻园研修之两大主题,昕夕读写,时在萦念之中。拟参加第二届江南文脉研讨会,提交论文即为《江南水德七义》。余动念以“水德”言说江南,亦有年矣。略说一义,即水之随物赋形,亦清亦俗,可矜可平,淡抺浓妆皆宜,上可陪玉皇大帝,下可陪卑田院乞儿。江南之水乡水镇,即世间而超世间,郦道元《水经注》,明言水乡区别于水域,后者为“神境”,前者介于神人之间,既得山川自然之灵气幽韵,又不离世俗人生之柴米油盐。盖江南之水乡古镇,非为现代人观赏游览而生,有其交通、物流、交易、洗濯、浣衣、避暑、打渔、灌溉以及取用之类实用功能,为乡人生活所浸润纠缠而不可须臾缺失之环境。白乐天诗“泓澄动阶砌”,“平池与砌连”,“池分水夹阶”,水与砌与阶之关系,即生活世界与自然世界连接之关系。然正如明人钟惺所论江南三吴水乡:“水之上下左右,高者为台,深者为室,虚者为亭,曲者为廊,……无非园者。予游三吴,无日不行园中,而人习于城市村墟,忘其为园。”“忘其为园”,即忘其为美,忘其为景,忘其为佳赏之所在也,所谓真美人不自知其美。藏妙于无,含敛而厚,将美消融于日常,是亦江南水德之一义也。
2.“命名”亦中国美感之特色。西方人取名,动辄托马斯、安德生、约翰逊,吾国则极具一套复杂精致文化。源于儒家所谓名教。儒家以其“名”之自觉,将宇宙、社会、人生之诸多方面,予以命名化。而道家则祛名化,此亦一好,两轮并行也。然文学家命名与儒道二家不甚相同。余尝驱车流连徘徊美国黄石公园七日之久,细读山川草木,广漠之野、蛮荒之林、热泉之地、幽深之谷,以及黑熊出没,稚鹿戏水,野牛挡车,飞瀑渟渊,奇花老树,极人间之绝美,尽天地之伟观,然终有一久长之憾:了无命名,一往荒芜,意乏回味,美则美矣,意兴、观想、神思,均未在场。目击而道不存,身接而心未通,此亦西方风景之大阙失也。吾国极佳之风景,均以诗人命名而来,如辋川之竹里馆、辛夷坞、鹿柴、北垞,而诗人王维又由《昭明文选》中取谢诗之名句名景而来,分明虚构一幅心画,即宇文所安所谓文本化之山水世界,以区别于长安城之贵族世界。余在孔学堂,亦喜命名,曾有“无尽藏台”(又名花溪第二景,暂无第一)、“半山亭”、“酥雨轩”之类命名,与刻石雕楹,了无干系,其心境故事,略同于摩诘也。
3.今日孔学堂开有关生态文化智慧小型学术沙龙。余讲及三义。一曰“返自然”,人类当今之于生态文明之自觉,乃一大趋势,一大潮流,一大事因缘,即倾科技、宗教、哲学、文学、政治、教育及经济之力,以“返自然”。此“返”,极具人力、极具功夫,绝非无为,绝非消极自然、原初自然,自己而然,随笔曾有札记,理据此从略。至今浩浩荡荡,方兴未艾,文学及古典学研究,恰逢其机,即所谓“预流”也。二曰“破体系”,十九至二十世纪之知识体系,学科分割,学术孤岛,专业自限,理性傲慢,科学崇拜,技术专家主义,西方学人早有反省。生态文明及智慧,须更多